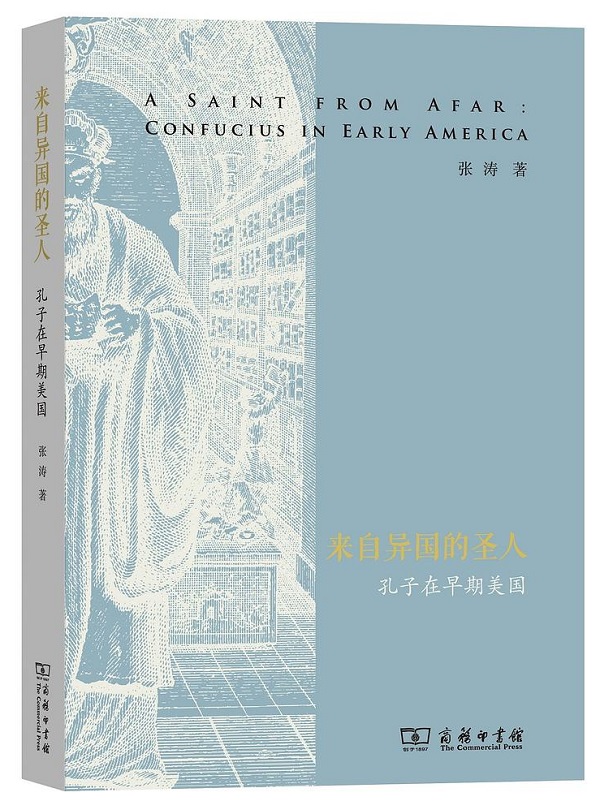
作者:张涛
孔子也会现身美国人谈论国际事务的各种场合。在早期美国的外交视野中,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相互体恤和对等交流等原则被视为国家之间应该遵循的交往准则。美国早期著名政治家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 1811~1874)表达了这一认识。1845年的美国独立日,萨姆纳在波士顿市政厅发表演讲,抨击国际交往崇尚武力的倾向。萨姆纳认为,基督教不仅坚持仁爱至上,而且拒绝暴力。为增强基督教和平交往原则的说服力,萨姆纳进一步指出,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准则的内涵,孔子不但认同此说,而且将其纳入国家治理应该遵循的九条准则之中。然而,令萨姆纳忧虑的是,世界各国即使在和平时期,亦是枕戈待旦,丝毫没有实践基督教和孔教原则之意。但具体到中国的外交处境时,这些原则又因为中国的迂腐而成为其对外交往的桎梏。
以孔子批判法国革命
批判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让美国的外交舆论首次集中引用孔子。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美国人曾经欢欣鼓舞,视其为美国革命的延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革命日渐走向极端,践踏自由权利、偏激的世俗化以及无政府主义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令美国人深感震惊。孔子讲究的中庸、平和,与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衬托出法国革命的非理性色彩,这是美国文献竞相强调的一点。
首先,法国革命以自由、权利为口号,革命者却在夺取政权之后肆意践踏公民权利,让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不寒而栗。各种文献以孔子及其思想为参照,向美国民众形象突出了法国在革命之后的这一现状。1797年,数家报纸登载的短文尖锐指出,法国人似乎混淆了自由、共和主义和怀疑嫉妒,“在法国革命的历史中…野心是如此频繁地蛰伏于爱国主义的表象之下”。雄才伟略与仁爱之心无法两全,权力欲望与祸国殃民却如影随形。作者不禁引用戈德史密斯的话哀叹道,“大自然似乎已经忘记,当初如何塑造了孔子或苏格拉底的大脑”,因为她如今塑造的,尽是自私自利之徒,这些人“毫不考虑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在此背景之下,真正关心民众权利的政治家遭到攻击和排斥。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就是一例。1798年的一份美国出版物称其“道德高尚”,“正是(法国)革命的孔子”。但米拉波却备受陷害,法国“人民当中仅存的人性光辉”可能因此熄灭。米拉波拥护君主立宪,属于法国革命中的温和派。美国印刷称赞米拉波的小册子,表明美国人反对法国革命的极端主义和蔑视公民权利的行为。
其次,法国革命偏激的世俗主义令美国人深感不安。虽然美国社会赞成政教分离,但并非反对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拥有更加自由的信仰空间。法国革命试图破除神学,迫使人们仅从自然界寻求真理,美国人对此难以认同。1790年8月18日,美国报纸转载英国文章声称,法国革命哲学家的“致命”错误,是蛊惑人们抛弃看似眼花缭乱而又神秘莫测的神学,转而“透视自然,寻找自然之神”。作者将此举比作中国皇帝因为独尊孔子,而搜缴和烧毁其他信仰著作的举动,表现出“无耻行径的所有特征”。1795年8月3日,《联邦消息及巴尔的摩每日商报》刊登文章,称宗教为“所有长久政府的基础”。作者表示,尽管从长远来看,美国和中国等可以没有国教,但不论孔子,还是美国各州的开创者,都未敢忽略宗教情感的社会价值。法国人“轻率亵渎宗教”,结果可想而知:“自由之名被暴虐、最残酷的(政治)目的所玷污”,法国人的英勇气魄为“野蛮的暴行和贪婪的掠夺”所取代。
帕斯多雷(Pastoret, 1755~1840)是法国民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法国革命之后的遭遇映射出专制政府的极端世俗化倾向。据称,在法国革命之前,美国人就已经熟知帕斯多雷的宗教研究著作,其中包括针对孔子等人的比较研究。他还出版专著,研究摩西。这些论著散发出“研究与自由精神”。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浓厚宗教情结的人,却不愿充当革命之后成立的国民议会的代表,因“厌恶其程序”而辞职。美国报纸相信,“自由之友”永远不会忘记帕斯多雷。早期美国将帕斯多雷从宗教角度对自由的探索与孔子联系起来,意味着认可孔子思想在宗教层面的宽容情怀,突出帕斯多雷不愿与法国革命者沆瀣一气,则意在显示法国革命对于自由的破坏。
其三,法国革命让本已剑拔弩张的英法关系雪上加霜,美国人在看待两国敌对情绪时,也有引用孔子、反对法国无神论和极端主义的情形。法国革命废除君主制、破除神学的举动引发英国严重不安,后者惧怕自己的政治与宗教制度遭受动荡之虞,甚至因此拒绝与法国革命政府进行谈判。关于此事,美国的报道是,虽然很多英国官员以法国已经皈依无神论为由,力主政府关闭谈判大门,但还是有人希望与法国谈判。主张谈判的英国人质问政府:孔子门徒是“宇宙中唯一固定的自然神论群体”,为何英国愿意向他们派遣使团,而对法国却不愿如此?从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英国政府显然没有采信反对意见。这些信息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是,英国政府相信,即使是孔子学说,都优于法国的无神论。在此问题上,美国人站在了英国人一边,正如1793年5月多家美国报纸在转发这一新闻时所说,“阅读英国人关于对法战争或和平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横亘在谈判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就是法兰西民族所谓的无神论”。
1791年6月,英国下议院激烈辩论魁北克法案,这让美国人再次见识了英国戒备法国的心理,加深了对于法国激进主义的疑虑。魁北克本是法国殖民地,后割让英国,成为加拿大殖民地的组成部分。但魁北克地区的居民仍以法裔为主,英国在制定政策时也必须考虑这一特殊性,其魁北克政策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英国的对法态度。根据美国报纸的报道,议员的辩论焦点是,英国是否应该在魁北克照搬法国政治模式。法国大革命的极端主义及其导致的社会混乱,让辩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情形。很多议员表示,因为革命,法国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曾经攻击人类的祸害被全部释放出来”,法国模式不宜模仿。仅有一名议员极力反对此说,宣称敌视法国的议员是在利用特权,“用最粗俗的言辞,诋毁任何他认为值得诋毁的法律体系”,法国宪法和孔子学说都可能因此成为攻击对象。然而,其他议员却反对这种比喻,声称以激进和混乱为特征的“法国病”(French Malady)远比其他政体逊色,如同在施行外科手术之前就必须重视的毒瘤。向报纸提供这一消息的美国人提醒读者,英国议会的辩论“清楚展现了该国在革命原则上的立场”。这名美国人显然认同英国议员区别对待孔子学说与法国革命政体的做法,也再次向美国社会展现了法国革命乏善可陈的一面。
美国的自主外交,源自独立战争期间联法抗英的权宜之计。战争一旦结束,“血浓于水”的美英之间重修旧好,法国则因为美国拖欠战时债务而对美国心生怨恨。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让美国疏而远之,美法同盟荡然无存。早期美国文献对待法国的态度既反映了这种恩怨变迁,也强化了美国社会警惕法国的情绪。孔子因其深受人类社会尊崇的地位,在早期美国的外交认知中,代表着理性的社会发展准则,是显现法国革命可惧与可憎特点的话语符号。
而在其他涉及外交的场合,美国人同样大力谴责违背这些准则的行为。比如,1846年的美国一位论教派(Unitarianism)会议上,名叫乔治·S·希拉德(Geo. S. Hillard)的演讲者目睹国家之间的交往现状,忧心忡忡。他指责说,国家间交往被自私欲望所主导,不仅低于“基督教的义务标准”,即便对照孔子和柏拉图等“讲求美德的异教徒”所制定的原则,同样不合要求。希拉德特别提到美国当时与英国和墨西哥都存在的领土争端,批评很多国会议员在辩论时表现出咄咄逼人、贪欲过剩的特性,违背前述对外交往准则。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卸任总统多年之后的1839年5月21日,也在致美国公民的公开信中,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亚当斯以英国对待美国的态度为例,说明总有国家乐于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认为,英国政府以及绝大多数英国人不愿正视美国独立的现实,而是把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等革命者视作“叛乱分子和背信弃义者”。但亚当斯相信,此举阻挡不了美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因为“不论在君士坦丁堡和北京、伦敦和巴黎,还是在查尔斯顿和费城……也不论是在亚伯拉罕和所罗门时期,还是琐罗亚斯德和孔子时代”,奠定美国国家身份的《独立宣言》始终是无法否认的真理。孔子当然无法知晓身后两千多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亚当斯仍然引用,意在证明《独立宣言》包含了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也下意识地称赞了孔子思想与美国观念的契合。
透过孔子看中国
在评论中国的外交表现时,美国文献更会引用孔子。但此时的孔子在指示中外交往应该应用的理念之外,还喻指僵化遵从孔子中庸、平和原则,从而遭受列强——尤其是英国——蹂躏的中国,是一对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本来可以避免中西矛盾升级,或者让中国免于失败,但不论是中国还是代表西方的英国,其所作所为都与孔子的要求相去甚远。1839年,林则徐禁烟成功,《纽约福音传道者》杂志称,销往中国的鸦片贸易终于结束,“我们由衷地感到满意”,林则徐的措施“迅速而有力”,是世界任何国家“为保护民众健康和道德而采取的最伟大的策略之一”。但赞许之余,文章不无痛惜地指出,中国禁烟之所以耗时如此漫长,根本原因在于英国人和其他商人的贪婪,也在于“中国人的腐败”。后者频频背离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与英国人沆瀣一气,毒害中国百姓。后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有美国文献以幽默的口吻宣称,这是由于中国的指挥者缺乏孔子的智慧。例如,1846年,广州城防再次遭到英国军队的狂轰滥炸,中国守卫者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无奈之下,他们派出信使,向英军建议,双方子弹和炮弹只填火药,不装弹头,既可节约弹药,又能避免生灵涂炭,中国皇上也会龙颜大悦。针对这一不可思议而又显得怪诞的提议,美国媒体揶揄道,看来唯有“孔子的所有智慧”才能拯救身陷逆境的守城者。
英国人走私鸦片的行为同样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1840年11月,《浸礼会传教杂志》刊文,严厉抨击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认为他们既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也在孔子道德的水准之下。文章指出,如果一个人因为无知而在无意间给他人造成了伤害,别人会感到遗憾;但如果为了贪图利益而故意毒害他人的健康和道德,他迟早会让别人感到恶心,产生憎恨。英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她信奉基督教,本应充满正义和宗教情怀,却为了增加一丁点财政收入,居然鼓励种植毒品,并偷偷把毒品运入一个辽阔帝国的内陆,损害三亿人的身心健康。杂志责问英国人,“在孔子门徒的眼里,这种行为如何能提升基督教和欧洲政策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示,英国走私鸦片的行径既违背了孔子对于国家交往之道的要求,也玷污了基督教和欧洲国家的名声。
另一方面,美国人目睹中国的不堪一击,内心充满着怒其不争的情结,把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僵化遵循孔子的中庸、平和原则。通过鸦片战争,英国从中国窃取了大量好处。美国人虽然颇有微词,但鄙视中国的程度明显超过对于英国的不满。1843年2月4日,《纽约技工》杂志刊登“可怜的中国”一文,大力贬低中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的表现。文章轻蔑地写道,在攻城略地,获取金钱,“杀死一批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以及一些真正的男人”之后,英国人“正在举行强盗的狂欢”。中国人同意割地赔款,而如果他们信守承诺,就是“懦夫”,如果言而无信,则成了“无赖加懦夫”。在作者看来,“可怜的中国”犹如“臃肿、羸弱、缠绵病榻的老妇人”,“孔子的贵格教”(Confucius's Quaker religion)与中国人逆来顺受的性格、如同洗衣盆的帆船以及一无是处的武器和防御堡垒,完全无法阻挡外敌入侵。正因为如此,“英国的罪恶行为可能会激起我们的愤怒,但我们对于中国人,不是怜悯,而是鄙视。如果他们表现出男人的气概,我们会敬重他们,为他们感到悲伤”。文章最后说,“至于那些懦夫和白痴,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没有游泳的勇气,就让他们沉下去吧。”
同月18日,《乔纳森兄弟》杂志出言相似,宣布“(英国)对华战争结束了——孔子应该受到表扬”,身为英军指挥官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因为侵略有功,为伦敦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茶叶供应,应该擢升为“熙春茶勋爵”(Lord Hyson)。作者讽刺说,既如此,英国应该把伦敦的饮用水源地新河水库改造为“巨大的都市茶壶”,在水库下面建造锅炉,四通八达的管网将把茶水输送到城市的任何角落,火车和邮局则负责把茶水送到英国的其他大小城市。文章还说,“据传”,英国国王有意邀请欧洲各国的君主,前来参加一次巨大的茶会,但美国总统不在受邀之列,“因为他‘太庸俗’”。
如果英国在中国稍微文明一点,不那么咄咄逼人,美国文献就会对英国人的行为表现出明显的认同感,说明美国人不论如何同情中国,根本上还是希望西方能够打开中国的国门,迫使中国按照西方的规则行事。以下事例可资为证。1842年12月,广州谣传,英国商人将在被称作“河南”的珠江南岸地区获得新的土地,引发部分当地居民激烈反应,英商财物部分受损。美国《阿尔比恩》杂志报道,在类似于纽约坦慕尼协会会堂(Tammany Hall)的广州明论堂,民众聚集,群情激昂,纷纷谴责英国人的做法。然而,杂志发现,有“广州博学者”发表公开声明,让市民冷静。声明说,孔子教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但英国人的举动尚不足以构成近忧,鼓噪者也没有深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博学者”表示,英国人的真实目的,仅在于与中国人比邻而居,和谐相处,而不是使用暴力,所以,爱国者应该实践孔子的另一语录“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同前),不轻易诋毁或称赞他人。杂志尽管声称,将在获取更多信息后,再对事件作出评判,但其偏向已经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了。它声称,“博学者”的声明是“一份真正温和而又切合实际的文件…它明确无误地证明,英国军队在中国的行动是富有人情味的”。
有少数评论不但直接为英国的胜利而喝彩,而且认为孔子及其思想也应该被“先进的”西方文明所取代。1840年12月,《纽约明镜》杂志发表文章,谈论蒸汽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作者认为,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在缩短全世界时空距离的同时,还将“连接思想,把所有个人的思想融合为一”。在此背景之下,新的思想将迅速降临“愚昧无知的亚洲”,“在不可阻挡的蒸汽力量面前,亚洲的古老传统支撑不了多久!”文章难掩兴奋地宣称,英国舰队已经启程,前往黄海,教训钦差大臣林则徐。如果中国陈旧古老的城墙在英国炮火之下轰然倒塌,天子把领地让给西方的理性思想,“约翰牛在北京的大街上推搡孔子的后代”,那“并非出乎预料,而是极为有趣之事”。1846年9月5日,就连远离美国本土的火奴鲁鲁《波利尼西亚人》报也对英国在华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该报表示,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主要政治原则正在迅速扩散到全球,比如英国的胜利,就给中国带去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和“让孔子思想黯然失色的道德体系”。报纸所担心的,乃美英今后如何调和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矛盾,避免直接冲突。
英国通过战争获取诸多特权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对华官方关系。但由于美中之间还没爆发激烈冲突,文献在把孔子与美国对华官方行为联系在一起时,没有着重体现要让孔子彻底臣服的强硬心态,而是仅仅把他视为美国及其使华官员需要悉心了解的中国象征。1843年初,美国国会决定批准向中国派遣使节,并拨款40,000美元。《缅因耕耘者》报提前获知并报道了这一消息,认为此事“极其重要”。该报预测,通过建立官方关系,中国这一“未知地区”(terra incognita)将为美国人所熟悉,就如同大西洋对岸普通的欧洲国家一样。报道相信,描述中国道德与风俗的书籍将应运而生,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也将出现,甚至三卷本的《现代孔子与中国现状》(The Modern Confucius, or China as It Is)都有可能在几年之内由美国极富盛名的哈珀斯(Harpers)出版社推出,为各大图书馆所收藏,方便美国社会了解中国。
到了美国真正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文献同样注意到孔子对于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在国会批准遣使决议之后,美国总统委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顾圣为前往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据称,顾圣知道,中国人“拘礼而又谨慎”(punctilious),在取名方面尤其如此。所以,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他在确定自己的中文名字时,选择了“顾”和“圣”两字,因为根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顾”表示“看、尊重”,而“圣”则通常与孔子和其他圣人联系在一起。选定“顾圣”为其名,意在表明特使尊重中国的孔子等圣人,希望以姓名为突破口,顺利开展谈判。顾圣之名是否真的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展,似乎没有资料能够佐证。但顾圣来华之后,虽然公务繁忙,依然抽出时间,学习中国皇室使用的鞑靼语,并且精选包括孔子著作在内的大量鞑靼语书籍带回美国,则是有据可查的。1845年3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义华业(Alexander H. Everett, 1792~1847)为顾圣使华之后首任驻大清国专员,但因专员无法接触中国皇室,故美国政府未明确界定义华业的具体职责。《波士顿信使报》建议,义华业应该利用充裕的业余时间,编辑孔子著作,添加具有同等哲学深度的批注,以此加深对于中国的认识,方便日后的工作。
由此可见,早期美国总体上还是肯定了孔子倡导的国家交往之道,也把孔子视作了解中国的窗口。但论及中国在与英国对峙时一触即溃的表现,美国人又惯于从孔子身上寻找原因,认为中国僵化坚持孔子的中庸平和之道,是中国缺乏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这说明,美国文献在对待孔子的外交寓意时,表现出长期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赞赏孔子提出的思想原则,一方面又因为蔑视中国的羸弱,而贬低孔子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出现在美国整个政治文献中的孔子,其遭遇展示了同样的两面性。当人们谈论政治人物的素养和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时,孔子的正面形象便出现了。孔子重视的政治家个人修养、德政仁治和外交准则等被频繁引用,成为美国社会评判政府、政策和政治人物的重要参照之一。但在与现实的中国相互联系时,孔子的形象就会明显下降:他或者因为自己的异族身份,衬托出美国某些政策和人物崇尚空谈、不务正业的弊病,或者因为中国的对外困境,被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伟大思想的世界普适性和国籍给予思想家的角色限制,在美国早期的政治话语中表现的非常清楚,并将在其他语境下发展出新的载体,见证着美国孔子认知二元线索的不断延伸。(本文选摘自《来自异国的圣人:孔子在早期美国》,张涛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出版。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