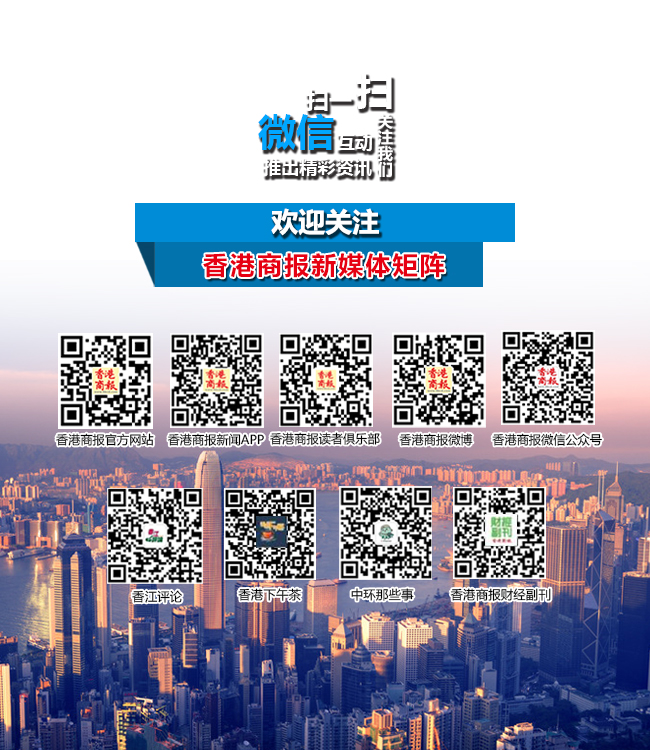廣受追捧的文學批評家安德烈・埃爾-柯尼希離奇死亡。因嫌疑重大而遭逮捕的作家漢斯·拉赫,不久前因其小說新作被埃爾-柯尼希大加貶損而向批評家當面發出了威脅。漢斯・拉赫的朋友,學者米夏埃爾·蘭多爾夫堅信其無罪,就此展開單方面的調查,過程中先後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警察、作家、 學者、出版家等等。他與他們逐一進行交鋒和對話。隨着調查深入,事件的樣貌被不斷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語的迷宮,懸念迭生,真相卻依舊隱藏在重重迷霧之中……
本文節選自德國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的小說《批評家之死》。

馬丁·瓦爾澤,德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1927年生于德國博登湖畔瓦塞堡,是當代德語文壇中與西格弗里德•倫茨、君特•格拉斯等齊名的文學大师。 主要作品有《驚馬奔逃》(1978)、《迸涌的流泉》(1998)、《批評家之死》(2002)、《戀愛中的男人》(2008)、《尋死的男人》(2016)等。 他曾于1981年獲畢希納文學獎,1998年獲德國書業和平獎,另外也曾獲黑塞獎、席勒促進獎等重要文學獎項。 其作品數度在德國引起強烈爭議。
一
既然大家並不期望我來撰寫我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東西,我就必須談談我為什麼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鬧得沸沸揚揚的事情。 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玫瑰十字會……感興趣的人都知道,這才是我的研究領域。 為了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進展的事情,我的確中斷了《從蘇索到尼采》一書的撰寫。 我所中斷的,與其說是寫作本身,不如說是為寫作所做的准備工作。 書的內容: 把個性色彩带進德語的,不是讓尼采獲益匪淺的歌德,而是蘇索,埃克哈德,伯麥。 由于資產階級文化精英的語言造就了我們的體驗能力和認知能力,所以我們,也就是讀者,看不出神秘主義者與歌德、與歌德之後的尼采一樣,有着強烈的自我意識。 只不過給前者带來快樂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說明,因為我在撰寫我的朋友漢斯·拉赫的故事的時候,有可能受我平時寫作風格的影響。 我們倆,漢斯·拉赫和我,都從事寫作。
出事的時候我在阿姆斯特丹。 我被約斯特·李特曼邀請去看他的收藏。 約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以及玫瑰十字會的手稿,數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家中間還找不出第二個。 我住在安博薩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這里,我是邊吃早餐邊看《新鹿特丹報》——我在阿姆斯特丹總是讀這份報紙——的時候得知漢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 報上說是謀殺嫌疑。 盡管我在國外總把讀當地報紙當作一種消遣,我還是趕緊去買了一份《法蘭克福匯報》。 報道說,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在他主辦的家喻戶曉、廣受歡迎的電視娛樂節目《門診時間》中抨擊了漢斯·拉赫的新作《沒長腳趾甲的女孩》。 節目結束後,這位批評家一如既往地來到他的出版商路德維希·皮爾格里姆的別墅,這幢別墅位于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擊的作家在此對他進行了大肆辱罵。 每播放一期《門診時間》,埃爾柯尼希的出版商都要在別墅里搞這麼一個聚會,至于說漢斯·拉赫是如何混進去的,這還是個謎。 別墅聚會的客人名單上並沒有漢斯·拉赫,按照慣例,一個剛剛“輪上”埃爾柯尼希的《門診時間》的作家是不會受到邀請的。
雖說漢斯·拉赫本人也在皮爾格里姆出版社出書,但依照出版社的規矩,他在那一天沒有資格到場。 很明顯,漢斯·拉赫想立刻對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報以拳腳。 據說,在兩個男仆把他架出去的時候,他喊道: 忍氣吞聲的時候過去了。 埃爾柯尼希先生等着瞧吧。 反擊從今夜零點開始。 參加晚會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學、媒體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對于拉赫這句話,他們不啻感到詫異,他們簡直深感震驚和厭惡,畢竟誰都知道安德烈·埃爾柯尼希的父輩中有猶太人。 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埃爾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車仍然停放在出版商的別墅前面,汽車的散熱器上面扔着他的黃色羊絨套頭毛衣,這毛衣大家都很熟悉,因為他在電視上總是將這毛衣挽起來搭在雙肩。 安德烈·埃爾柯尼希本人卻是無影無蹤。 那天夜里幾乎下了半米深的雪。 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 于是,第二天漢斯·拉赫有了謀殺嫌疑。 既然他拿不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也不想回答任何的問題,他很快就被收押。 根據有關方面的鑒定,他處于驚魂未定的狀態。
讀着上述報道,我呼吸都有點困難。 但我知道這不是漢斯·拉赫干的。 如果你用心觀察過一個人,你就會有這種直覺。 雖說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讀報時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 除了你,他沒有別的朋友。
我馬上給約斯特·李特曼打電話,告訴他我得馬上回慕尼黑。 我本想給他解釋我必須馬上回家的原因,突然又發現這話還不好說。 我只好對他講: 一個朋友陷入了困境。 要想准確表達自己的意思,有時候似乎還得像外國人那樣遣詞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了站台才想起看看落下什麼東西沒有。 我發現身份證不見了。 總台向我要過身份證,我因為走得太急,忘了要回來。 我給他們打了電話。 很快就有一個亞洲人模樣的小伙子把東西送了過來。 我沒有錯過自己選中的那班火車。 可是,火車走了一個鐘頭便停了下來,停在空曠的荷蘭大地。 我們沒得到任何解釋。 等到幾個乘客嚷嚷起來之後,列車廣播里才通知說: Deze trein is afgehaakt。 我們不得不下來等救援列車。 對我來說,這一切都和漢斯·拉赫、安德烈·埃爾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了關系。 我需要一個冷靜思索的機會,想想自己是否應該、是否必須、是否可以如此倉促地趕回慕尼黑。 我的想法很單純。 可是,當你腦子里開始計算、盤算、掂量的時候,反對的聲音就冒出來了。
漢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嗎? 名氣很大、幾乎成為明星的漢斯·拉赫,和僅僅在專業圈子里游蕩的米夏埃爾·蘭多爾夫算得上朋友嗎? 我跟他成為朋友,也許僅僅因為我們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鐘就可以串門? 他住勃克林大街,我住馬爾森大街,就是說,我們住在風景如畫的格恩地區的畫家村。 我們住在這個地方比較合適,伯根豪森不是我們呆的地方,漢斯·拉赫這麼說過。 他顯然比我年輕許多,看事情也比我樂觀。 我們倆都曾面带愧色地向對方承認,如果不是因為同住格恩區,我們倆成不了朋友。 他成天沉湎于五彩斑斕的寫作生活,從包羅萬象的長篇小說寫到一氣呵成的時事評論,我則一頭紮進群星閃爍的邊緣世界,一個由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構成的世界。 然而,當我們在韋森東克——這是一位對時事也感興趣的哲學教授——在格倫瓦爾德的別墅里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沒有理由不在告別的時候意味深長地說一聲“再見”。 我們倆都很吝惜時間。 我們稱不上什麼密友,這也許因為我們處理這種關系非常慎重。 而且我比他還慎重。 雖說我們在韋森東克的別墅結識不久便直呼對方漢斯、米夏埃爾,但這無非因為我們在國外,尤其是在英美國家走得比較多。 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說話的時候就叫我米夏埃爾了。
根據經驗,只有那些對我有好感,或者說那些為人真誠的才這麼做。 漢斯·拉赫具有真誠待人的天賦。 這我一下就感覺出來了。 我和他都不屬于這里的核心圈子,這個我們很快就注意到了,而且毫不避諱。 既然都住格恩,回家時我們合打一個出租,車費對半分,因為我們誰也不想,或者說不能夠讓對方請客。 我們倆一開始就顯得小里小氣,我倒覺得挺好。 我們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請的原因。 韋森東克向我問了一些有關卡巴拉的問題,因為《南德意志報》向他約稿,要他評論革舜·肖勒姆的一本書。 我當然沒好承認韋森東克所說的事情在我心里勾起一絲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覺。 對于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我可是再熟悉不過了,但是他們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熱衷于時事的韋森東克寫書評。 話又說回來,韋森東克在提問之前也說了,他們之所以向他約稿,他之所以答應寫這篇書評,完全是因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漢斯·拉赫認為,他之所以被邀請,是因為《法蘭克福匯報》對他不太客氣,甚至公然罵他是民粹主義者。 該報一位社長還親自上陣。 那天晚上韋森東克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試探,看他是否適合進韋森東克圈子。 他還說,我一定注意到韋森東克在提到那個發行人的名字時總要加上“法西斯”這一定語。 這個罵人的口頭禪明顯出自20世紀60年代。 當初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的那些人,現在雖然明顯有了老態,但還是不肯割愛。
盡管我——書寫划時代歷史巨著的人絕不會在閑聊中消耗夜晚的時光——哪兒也不去,可是累了我也翻翻報紙,所以我照樣知道誰和誰一帮,誰和誰作對。 余下的事情西爾伯福克斯教授會在室內樂劇院的休息廳或者在電話上向我通報。 正如他自己高高興興說的,他和上帝、和人類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電話號碼。 他高調地贊揚了我那本論述神秘主義的書。 他的頌揚既見諸報紙,也耳聞于廣播。 後來他又在室內樂劇院的休息廳里找我聊了起來。 他說有句話他真的憋了好久,可既然他已經第四次看見我坐在他前面兩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時也提醒我: 我們屬于同一個票區。 一聽說我家住格恩,他趕緊提醒我,漢斯·拉赫也住在那里。 他接着補充說,他的綽號就歸功于漢斯·拉赫。 他認為漢斯·拉赫給他起的綽號也可能出現在瓦格納的《紐倫堡工匠歌手》里面。
說到這兒,我只好承認我不知道他的綽號是什麼。 嗬,他高聲驚歎道,真有意思。 整個慕尼黑就您一個人不知道。 不過我自個兒傳播自個兒的綽號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他接着又說,漢斯·拉赫把他西爾伯福克斯教授稱為西爾本福克斯,是因為他有一次跟人聊天時把漢斯·拉赫前面再前面的一部長篇小說形容為作繭自縛的偉大作品。 在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麼地方說句什麼話,都會搞得路人皆知。 至少文化圈里是如此。 哪兒的文化人也不會跟慕尼黑這帮子似的喜歡流言蜚語。 就這樣,他在休息廳里對着我滔滔不絕,他的話匣子是在他證明他是哈拉興的居民、我又表示自己熱愛格恩之後打開的。 對于一個文學教授而言,格恩就是漢斯·拉赫的同義詞。 對于那片可愛的小市民住宅區來說,由于響起了入場的鈴聲,他加快了說話速度,漢斯·拉赫的名氣也可以說太大了點。 他早該搬到伯根豪森了,教授繼續說。 從他的音調和微笑可以判斷,他的話带有諷刺意味。 教授講這句話,當然沒有影射我沒有資格住伯根豪森而只配住在格恩的意思。 可是我沒法不聽出這層意思。
世上沒有一個警察會認為我有謀殺嫌疑。 但是他們會懷疑漢斯·拉赫,盡管他殺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樣微乎其微。 當我在報紙上閱讀有關漢斯·拉赫的報道時,我沒有考慮他是否需要我。 我沒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國會有許許多多的人來帮助漢斯·拉赫擺脫這一荒唐的懷疑。 我沒法想象任何事情。 我甚至沒法想象自己會給人多管閑事的印象。 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無非偶然做了他的鄰居。 平時我很容易臉皮薄。 現在我的臉皮卻一點不薄。 我必須去。 馬上去。 去慕尼黑。 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
二
在大門口迎接我的警察說: 頭兒要親自接見。 多長時間,我問。 他說: 換了我,充其量半個小時,至于頭兒,他願意搞多久就搞多久。 反正所長大人知道他拘押的是誰。 在一個漆成警察綠的房間里,我被安排坐在一張小圓桌旁邊,小圓桌擺在房間犄角,隨後所長大人就带着拘押犯走了進來。
漢斯·拉赫和我在房間的一個角落隔着小圓桌坐着,所長大人的辦公桌放在另一個角落。 所長大人似乎要表明他不想監聽我們的談話,所以馬上開始研究文件。 漢斯·拉赫望着我,聳了聳肩膀,然後講了一句與其說給我聽、不如說是給所長大人聽的話: 煙是可以抽的。 警官說: 可以抽煙。 漢斯·拉赫又說,今天所長大人的情緒一看就特別地好。 所長大人問他有沒有什麼可抱怨的。 我告訴您,漢斯·拉赫對我說,所長大人每年都飛到尼泊爾度假,然後總是带些錄像带回來給犯人們看。 在那座山後面,您從這兒也看得見,他接着說,有一家英國酒店,我們在那里喝過瑞典啤酒。
拉赫先生很快就打聽了我的情況,所長大人說道。 但他通過音調表示他繼續專注于他的工作,無意參加小桌子旁邊進行的交談。 他只想傳達一個意思: 漢斯·拉赫和我別以為他在竊聽我們的談話。 公務員比人們想象的要勤快許多,漢斯·拉赫說道。 說了這話他就一聲不吭了。 如果這位公務員再說點什麼,他肯定也會再說點什麼。 他望着我,但並沒有看得我非問一句“您好嗎? ”不可。 我從他的眼神里看不出半點期待或者好奇。 他打哈欠了。 但他很有禮貌,想掩飾自己的哈欠。 我望着他,不知道這話從何說起,但時間越長,我越不覺得難堪。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告訴他我知道不是他干的。 安德烈·埃爾柯尼希以他那種方式來評判作家,必然要四面樹敵。 為什麼偏偏是漢斯·拉赫失去控制呢! 有些人在埃爾柯尼希那里的遭遇比他慘多了。
西爾伯福克斯教授向我透露了許多內幕,多得讓我都不想再往下聽。 我希望漢斯·拉赫理解我為什麼到這里來。 我想替他做點事。 我來這里,是一種主動的姿態,他得做出反應。 他坐在那里望着我,平心靜氣。 他對我沒有任何期望。 也許是因為他的出版商已經給他請了最優秀的律师。 也許因為他天天都要在這張小桌子旁接待許多男女朋友。 突然間我覺得自己是多余的。 我真應該呆在阿姆斯特丹欣賞約斯特·李特曼收藏的卡巴拉手稿,忘了慕尼黑吧,明天共和國各大報紙的文化專欄就將謳歌漢斯·拉赫,他會接受一個又一個的采訪,那可憐的家伙,那個真正的凶手會一點一點地坦白,他的母親是妓女,他是在孤兒院長大的,神甫的助手強奸過他,他十七歲起作奸犯科,二十八歲——正好是他再次出獄的時候——寫自傳,寫好之後把稿子寄給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埃爾柯尼希通過女秘書轉告說,他那里不是回收蹩腳傳記的垃圾站,這話在作者心中點燃了仇恨的火焰,他在電視里看見了埃爾柯尼希,趕緊打聽在什麼地方,看門的向他透露了慶祝活動的地點,他迫不及待,在紛飛的大雪中耐心等待,大明星剛一出來,他便上前一陣亂捅……
我冒昧造訪,請原諒。 這話我也說不出口。 這太草率了。 這是一種感覺。 感覺總是草率的。 感覺可以草率。 感覺必須草率。 事實如此。 幸好他不需要我。 我又能為他做什麼呢? 但是我從他的眼神里看不出“您來這兒干嗎? ”的疑問。 他平心靜氣地望着我。 不表態。 也幾乎不流露任何情緒。 他在撓自己的手背。 他絲毫沒有怪罪我的意思。 我們相對無言,我們一點也不難堪,我覺得自己和他達成了某種默契。 他並不認為我來這里是多管閑事。 除了他,我還能和誰一聲不吭地坐上一個鐘頭? 他還能和誰……嗨,他倒是可以,也許他都習慣了他不說話別人也不說話。 假設我明明看見他不想說話卻又沒話找話,那我可就弄巧成拙了。 就沒有經受住考驗。 是這樣的。 名人可以為所欲為,他永遠正確。 只有你會犯錯誤。 即便你不承認這種游戲規則,你照樣會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行事。 但既然你和他相對無語地坐了一個鐘頭卻又不覺得尷尬,那你也應該心滿意足了。 算了。 保持自由。 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着好玩。 保持自由。
後來還是所長大人提醒說時間到了。 他沒有對我們的沉默做什麼評論,這出乎我的預料。 他本來可以說,兩位先生一點沒有妨礙他看文件,對此他深表贊賞。 他絕口不提我們默默無言的事情,這倒是好事。 有水平,我想,所長大人有水平。 兩人陪我走到門口。 既然我不想拿無聊的挖苦或者半生不熟的諷刺來殺風景,所以我在告別的時候跟先前一樣沉默不語。 但是我盡量不讓這種沉默變得激情澎湃。
最後,漢斯·拉赫從夾克衫口袋里掏出幾張手寫稿交給我。 他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呼吸到清新的冷空氣之後,我才知道那屋子里有多熱。 暖氣燒得太熱了,這種情況在機關衙門屢見不鮮。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再次體會到什麼叫輕車熟路。 我腦子里想的是他,浮現在眼前的還是他,我沒法擺脫他,因為我先前認為他平心靜氣,現在才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兒。 他什麼都無所謂,沒錯。 可是他平心靜氣嗎? 他的形象浮現在我的腦海里,我看見他那無助的眼光,看見他的紅頭發,那是一頭灰中带紅、短得不能再短的自然卷。 即便他有意蓄發,我們也無法想象這樣的頭發如何變長。 他的額頭又高又圓。 他的眼眶很淺。 噢,漢斯·拉赫。 他的樣子我看了又看。 我可知道,他和我相向而坐時並不是平心靜氣,他一直在——吸煙。 我甚至沒有數他抽了多少支煙。 本來我是有時間做這事的。 一言難盡。 漢斯·拉赫。 我用自己所熟悉的歐洲語言輪番讀這個名字,看看有什麼效果。 我這是在逃避嗎? 但願不是。

馬丁·瓦爾澤
三
當白雪把一切,把所有新蓋的建築物覆蓋之後,格恩最能顯出舊日的風貌。 冬天的大雪似乎每年都有一兩次顯示威力的機會。 當路面還沒有清掃,當路上的黑人影兒為了保持身體的平衡,不得不揮舞雙手的時候,我的工作效率最高。 假如沒有介入這件事情,我現在本應奮筆疾書。
回家之後,我發現自己還是不清楚漢斯·拉赫處于什麼狀況。 他沉默不語。 什麼叫沉默。 我們在沉默中學習語言! 在詞不達意的時候學習語言! 相向而坐,一聲不吭。 怎麼能把這種狀態稱為沉默不語呢。 我為他感到惋惜。 事實如此。 我現在才承認: 我為他感到惋惜,因為我相信可能是他干的。 對我來說,殺人總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有時候——幸好是偶爾出現——我會做這樣的夢: 我殺了人,我有了殺人嫌疑,眼看自己就要被繩之以法,為了逃脫法網,我只好再殺死一個人。 夜里做了這些夢,白天我總是樂不可支。 我一整天都在樂,我恨不得引吭高歌: 我沒有殺人,哈利路亞!
我之所以倉促離開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趕赴施塔德海姆,是因為我相信這事的確可能是他干的。 沒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了。 所以去找他。 然後一聲不吭地坐在那里。 原因很簡單,如果某某人殺了人,你又有什麼話好說呢。 現在我發現我不替死者感到惋惜,我惋惜的只是他。 被殺死的人不再有痛苦。 可是殺人者呢……他無時無刻不在回憶下手那一刻的情形。 這事要是出在我身上,我會馬上自殺。 這不是為了懲罰自己,或者說贖罪。 而是因為我無法忍受永恒的、揮之不去的回憶。 剛才他坐在我對面看着我,平心靜氣。 我盡量讓自己相信這點。 平心靜氣。 他筋疲力盡,一臉憔悴。 他肯定還沒有睡上一個安穩覺。 他的眼睛。 現在我才明白他的眼神的含義。 這是什麼都無所謂的眼神。 我想一個人呆着。 我不需要關心。 請注意: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合適。 我只配做子虛烏有的事情。 我竟然把他這種心態闡釋為平心靜氣。 我竟然做出這種闡釋。 我追悔莫及。
我坐不住了,我無法陶醉于外面的雪景,我在屋子里來回走動,直到我想起漢斯·拉赫的手寫稿。 趕緊讀。 這是幾張B5規格的活頁紙。 活頁紙的行距太大,所以他沒有貼着線條寫。 他的字跡很潦草。
親愛的米歇爾·蘭多爾夫,我開始閱讀,這是我在埃特大街寫的札記。 我寫了兩天兩夜。 不管這東西今後能做什麼用,請妥善保管。 衷心的問候。 您昔日的鄰居拉赫。
我進入正文:
論身高。 首先我要承認思想于我無所裨益。 我靠的是經驗。 很可惜。 經驗比思想慢多了。 思想來得快。 思想來得容易。 思想不是藝術。 思想很偉大。 通過思想,人們可以超越煩惱。 這些事情是不可能通過經驗辦到的。 我最近那些難以忍受的經歷就很說明問題。 一言蔽之: 我越來越多地發現,跟我說話的人在交談的過程中變得高大起來。 也可以說: 我在與人交談的時候變矮了。 這是一種讓人難堪的體驗。 眾目睽睽的時候最令人難堪。 在飯館里。 或者——這個最糟糕——在電視演播室。 災難性的後果……不過——這是我最新的體驗——當別人以某種方式談論我的時候,我也會矮一截。 而且即便我不跟這些人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們正好在談論我,這種情況照樣會發生。 我坐在自家的書桌旁,我想從椅子上起身,我的雙腳卻夠不着地毯。 這倒沒什麼了不起的,因為我要是從椅子上跳下去的話,我的波斯地毯會讓我軟着陸。 夜里——我感覺這是最重要和最美妙的事情——我的身體將得以恢復。
早晨醒來的時候,我將恢復以前的身高。 現在仍然如此。 一米八二。 自從有了這種萎縮和重新長高的體驗,我天天都給自己量身高,醒着躺在床上的確不足以恢復平時的身高。 非睡覺不可。 況且每次通過睡眠恢復的效果都各不相同。 現在我是早晚量一次。 如果說我經常在晚上縮短十厘米,那麼在經過一夜不太安穩的睡眠之後,我就只欠兩厘米或者三厘米。 我聽說有一種鞋,穿上之後可以使身高增加兩至三厘米,人們卻看不出這是巧妙設計的結果。 我現在就要尋找這種東西。 如果睡覺的時候不做夢,也就是不受外界干擾,醒來之後我總能恢復到我的一米八二。 我還不認為這些都屬于心理分析醫生和心理治療醫生研究的范圍,我將通過記錄來追蹤這一經驗,使之變得直觀,甚至還由此得以克服。 無論如何: 經驗不似思想那麼容易控制。 思想使人成為主宰,經驗則使人無可奈何。 但是記錄下來會有所帮助。 這也是一種經驗。
我剛剛讀完,電話就響了。 是刑警三支隊的隊長韋德金德。 他說他領導一個專事偵破蓄意殺人案件的小組,現在受命調查埃爾柯尼希/拉赫案件。 您和拉赫相對無語的事情,我已聽說了,您別因此而放棄努力。 那麼多人要求前去探訪,但只有您受到了拉赫的接待。 拉赫只接待了您和他的妻子艾爾娜,其他人一概謝絕。 拉赫必須中止他的無聲抗議行動。 這絕對不是卓有成效的戰術。 他可能在打如意算盤,以為我們找不到屍體就無法控罪。 他錯了。 我們有沾滿受害人鮮血的毛衣。 案發之夜的鵝毛大雪暫時對凶手有利,這可能讓一個詩人產生幻覺,似乎到了春暖花開的時候,融雪會把他在那天夜里埋藏的東西悉數带走。 也許他把屍體拖過托馬斯·曼林蔭大道,再拖下陡峭的斜坡,再拖過河壩,拖到河邊,最後投入伊薩河。 凶手還真走運。 那天夜里下了將近五十厘米的雪。 他沒准兒聽過天氣預報。 不過,天曉得積雪融化之後會有什麼東西給暴露出來。 這些話我已經講給拉赫先生聽了,他沒吭聲兒。 可是您得到了他寫的東西。 作為警察,我對一個問題很好奇,請多多包涵: 那東西您讀了嗎?
電話鈴響的時候,我剛好通讀了一遍。
什麼內容? 刑警隊長韋德金德問。
埃特大街札記。
我們讓他在那個地方呆了四十八小時,韋德金德先生說。
聽他說話的口氣,他似乎斷定我和警察一樣急于破案,斷定我將竭盡全力與他們合作。 漢斯·拉赫是一個等着定罪的作案人,這似乎已成定論。 韋德金德先生說自己正在讀漢斯·拉赫的書,他說他對漢斯·拉赫的了解將更加深入,深入到拉赫並不樂意的程度。 他請求我千萬別以為他對拉赫先生抱有敵意,或者漢斯·拉赫有什麼地方不討他喜歡。 作為一個專事偵破蓄意殺人案件的小組負責人,如果碰到那些殺人方式極其冷酷或者凶殘、殺人動機極其卑鄙的案件,他自然要對其作案人窮追不舍,眼前這個案子倒不存在這類問題。 但這終究是一樁命案。 這是一樁即便不是最高級、也是比較高級的謀殺案。 作案人是藝術家。 說到藝術,特別是文學,他也是略知一二,因為他喜歡讀書,盡管他還沒讀過拉赫的書,但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了,他也可以把一個作家視為受害者。 即便不是刑法意義上的受害者。 目前他正在閱讀,或者說研究拉赫先前出版的一本書: 《犯罪的願望》。 他發現這本書的自傳色彩太明顯。 不過他得先看拉赫的新作《沒長腳趾甲的女孩》。
通過調查——說到這里他強調一點: 他沒有得到拉赫哪怕一丁點的配合——他有理由推測,這本書,就是說,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在《門診時間》對這本書的評論,使拉赫對埃爾柯尼希的積怨化為一股仇恨的烈焰,于是他失去了控制,于是他就如此這般。 如果能夠重現出版商在伯根豪森的別墅搞《門診時間》慶祝酒會的場面,這案子就告破了,到時候簡直可以把這案子當作一篇手稿放在拉赫先生面前,只需要他簽上大名。 他說這些話只有一個目的: 請蘭多爾夫先生鍥而不舍,不要被拉赫的反應吓倒。 每一樁謀殺案都是一場悲劇。 而且是完整歷史意義上的悲劇。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任其發生而不正確地加以評價,就是說,這時刑警隊長壓低了聲音: 我們必須將它吸收,將它吸收到我們的語言,吸收到我們這個習慣了悲劇的文化傳統,我們必須把這場悲劇化為自己的財富,我們只有通過——尊敬的先生——關心來實現目標,我們必須把經受悲劇的人從可怕的孤獨中拯救出來。 請相信我的話,這種事情沒有誰能獨自承受。 所以有我們。 所謂的人類。 請原諒。 我說: 話可不能這麼講。 然後他又變換了話題。 有人告訴他,拉赫先生在埃特大街和別人關在一起的時候,把整個的注意力都放在一個叫貝內迪克特·布萊特豪普特的人身上,目前這人幾乎天天都從施塔德海姆被押到那里接受審訊。 他韋德金德想知道的是: 拉赫的手寫稿是否對兩人的密談有所交代。 他在我們,也包括您,蘭多爾夫先生,面前一聲不吭,隨便碰到一個拘押犯反倒竊竊私語好幾個小時。
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我現在只知道不能把人家交給我的東西泄露出去。 我就這麼對他說的。 刑警隊長表示或者假裝表示理解。 不過既然我們還要打交道,他就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坐一坐。 去刑事大案組所在的拜爾大街。 他希望我不要一聽到刑事大案這個詞就緊張。 怎麼樣。
行,我說,為什麼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