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禾 中华书局1912
在为配合“整本书阅读”而出版的《红楼梦》(注解本)里,保留了启功先生1979年为《红楼梦》作注释时写的序。在这篇序言里,启功先生谈到 “读《红楼梦》需要注意的八个问题”,主要是想表达《红楼梦》中有些问题是“注释”这种体例无法讲明白的。现在读来,这篇序言对读者仍然有着醍醐灌顶的意义,它让我们抛开那些不必过度解读和纠缠的细枝末节,而关注文本本身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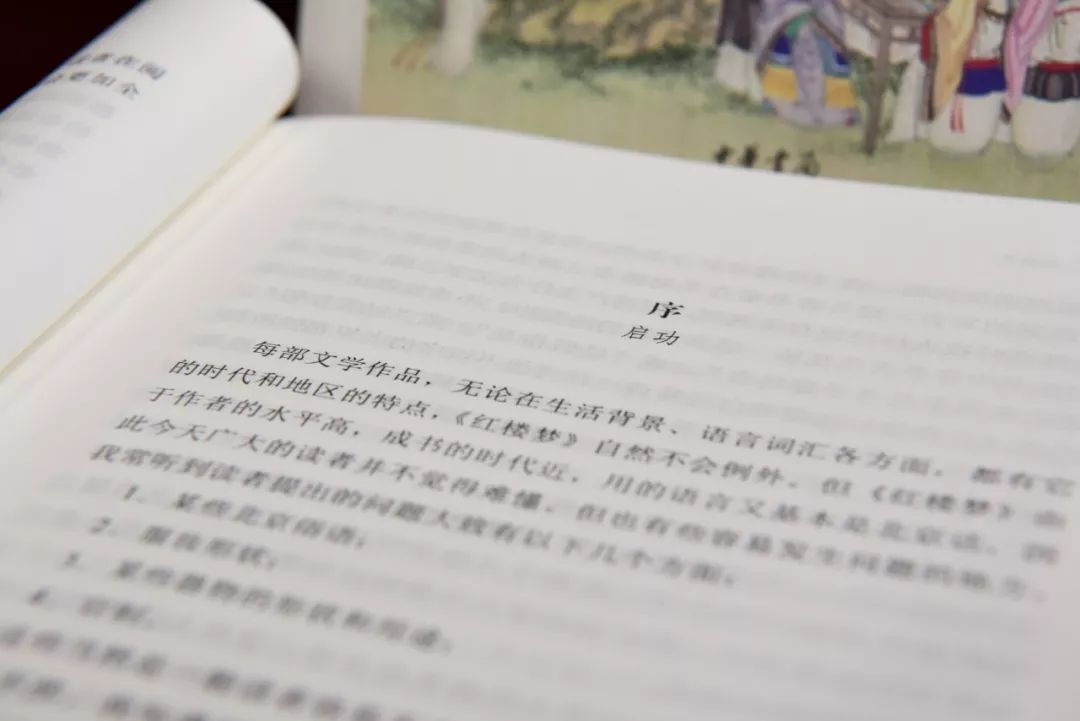
《红楼梦》(注解本)保留启功序
在讲到第八点“写实与虚构”的问题时,启功先生说:
作者虚构的手法,实是随处可见的。我曾把书中的年代、地方、官职、服妆、称呼、器物等等方面虚构的情况加以分析和统计,见《读〈红楼梦〉札记》,现在不必重复。我们据此可以了解作者由于有所避忌,所以他不但要把“真事隐去”,即在其他方面,小到器物之微,也不肯露出清朝特有的痕迹。
我们找到了启功先生1963年写的《读〈红楼梦〉札记》一文,由于篇幅较长,现选取其中有意思的细节和大家分享。
年代与地方
以年代而言,启功先生指出《红楼梦》和古代那些常首先交代故事时间地点的小说不同,作者在第一回中多次提到年代无考,“真事隐去”的说法,并借“太虚幻境”对联发表了一个声明: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以为,这大概相当于现代影视剧的开头“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声明,但显然前者却更辩证更耐人寻味。
启功先生举的最妙的例子是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一文,因为文体格式不得不备注年月日,于是作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
启功先生认为,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宝玉悲念追悼晴雯的心情,其实仍是为了巧妙地避开真实年代而使用的“障眼法”。
以地方而言,作者也常常真假参半。对于不止清代特有且著名的地方,常常用真名。如苏州(第五十七回)、湖州(第一回。也有人认为这一地名谐音“胡诌”)、大同府(第七十九回)等。还有一些纯属虚构的。如大如州(第一回)、孝慈县(第五十八回)、平安州(第六十六回)等。
又如我们常常觉得小说中的贾府在北京,但书中屡次提到京城时都用长安代替。如长安城中(第六回)、长安县(第十五回)等。此外也有很多“进京”“来京”的说法,但全书竟然没有一个“京”字上带有“北”字的。这就巧妙避开了清代的首都“北京”。说到这里,启功先生又加了一句:“固然明代的首都也是北京,未尝不可以强辩,但作者终于把它躲开了。”由此也可见作者运真实于虚构的严谨。

清《大观园图》(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官职
启功先生在序里已经提到作者在官职避忌上尤为严格,凡是清代特有的,一律避开。
所有的官职名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也有完全信手虚构的。即以历史上曾经真有的官名来说,却常常不是同一朝代的,或者那个官职,在古代并不管辖那种事务。也有清代的官名,但往往是清代沿用前代而非清代所特有的。
启功先生列举了很多官名,如第二回的“兰台寺大夫”,甄应嘉的官衔“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十三回贾蓉封的“龙禁尉”,其实都是作者信手拈来,或半真半假或残缺不全的。正如启功先生在序中说,像“龙禁尉”“京营节度使”等等,不但清代没有,即查遍《九通》、“二十四史”,也仍然无迹可寻。

《红楼梦》神游太虚图
服装
讲到服装,启功先生认为:
本书中人物的服装,有实写的,有虚写的。大体看来,是男子的多虚写,女子的多实写。女子中又是少女、少妇多实写,老年、长年妇女多虚写。女的官服礼服更多虚写,实写的只是些便服。
以虚写而言,我们先看男子的服装。其实书中提到男子衣着的地方很少,像贾政、贾赦都没有正面描述过他们的容貌服饰。第一回当了县令的贾雨村是“乌帽猩袍”,第六回对于贾蓉形象的描述是“美服华冠,轻裘宝带”。第十五回写到北静王时,作者给了他一身“戏装”:所谓“头上戴着净白簪纓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还有第八十五回只写“北静王穿着礼服”。这些地方都是虚写,而凡能代表清代制度的官服,一律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又如写到老年妇女贾母,在她出现的重要场合,如元妃省亲、进宫探视等,都写的是“按品大妆”。至于具体按什么品,每品的服妆是怎样的?怎样叫“大妆”,还有没有“中妆”和“小妆”,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作者只字未提。
以实写而言,男子中只有贾宝玉的服装算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人了。如第三回出场时描述的头戴紫金冠、脚登青缎粉底小朝靴等。启功先生说这里的“紫金冠”又名“太子冠”,只是小孩的游戏装束。
又如第四十五回通过黛玉的眼睛看到的是:“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还有其他很多地方的描述,服装都是红红绿绿的,不像成年男子的服饰,是娇养小孩的标识,何况还写他带着寄名锁、护身符等。
我们再看女子。比如对王熙凤第一次出场时的便服描写很具体,启功先生在序言里也有所提及,她头上戴的“金丝八宝攒珠髻”“朝阳五凤挂珠钗”,其实不过是暗写清代命妇所戴的钿子。其他如对宝钗、黛玉、袭人等少女和丫环的便服也有具体描写,但基本上都是说什么质地的棉袄什么样子的外褂什么颜色的衬裙,这些都是明代就有的习惯装束,清朝也都基本沿袭了。所以无论怎么写也不会露什么马脚。

87版《红楼梦》剧照
总之,无论实写还是虚写,曹雪芹在人物服装上都显示了他运真实于虚构的高超技法。因此,启功先生感叹:“我们现在的画家最困难的是画红楼梦人物图,某个人物的服妆,在书中写得花团锦簇,及至动笔画起来,又茫然无所措手了。”
启功先生还分析了人物的发辫,指出“发辫是清朝特有的装束,但小孩的发辫却不止清朝独有”。书中有几处写到宝玉的发辫,但都是小孩的发辫,没有一处提及过成年男子的头发。这就完美避开了清朝独特的“大辫子”。只有第七十八回写宝玉“ 靛青的头”,似乎若隐若现,但也仅止于此。
称呼
关于称呼,启功先生也发现了一个现象。
《红楼梦》中的亲属称呼都很通俗,如哥哥、兄弟、姐姐、妹妹、姨妈、舅舅、婶子、姥姥等等。只有对于直系尊亲属的称呼,始终含糊。
例如贾政、贾琏、宝玉、黛玉、秦氏、贾兰等称贾母为“老太太”,王夫人、贾珍、李纨、贾琏、宝玉等称贾政为“老爷”,王熙凤、秦氏、探春、宝玉等称王夫人为“太太”等。这些地方都用了官称。
启功先生认为,封建官僚家庭中的称呼是非常严格的。子女对父母或称爸妈,或称爹娘;对祖父母多称爷爷奶奶,都不许用官称。而清代旗人更有自己独特的称呼阿玛、额涅等。为什么本书一律用了官称呢?启功先生揣度,这也是作者的隐藏之笔,是不肯露出清代的特点而故意为之的结果。
除此之外, 启功先生还例举了其他很多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从没详写过妇女行礼的形式。男子行礼时也只写“以国礼相见”,究竟“国礼”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这和前面“按品大妆”是一样手法。比如作者写到栊翠庵的大树红梅,又写到笼地炕,地方南北,使人莫辨。又如写到太虚幻境、十二钗画册、秦氏之死、真假宝玉等地方,也常常使人迷离恍惚。
为什么曹雪芹必须这样煞费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呢?启功先生推测的原因可总结为两点:
外部就是怕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注意而招致祸患,即清朝人都惧怕的“文字狱”;内部就是作者是带着忏悔、惋惜的目的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写这部小说的,曹雪芹既以自己家族、亲戚的生活为主要模型,肯定不愿十分露出模型中的真人真事而免得有人对号入座。
启功先生所举的例子,正是作者“隐去真事”中最巧妙不易察觉的地方。如此完美回避,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理解为什么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同时也能察觉启功先生对《红楼梦》关键问题的解答就像“当头棒喝”,虽然文字不多,但足够切磋琢磨。



